阅读:0
听报道
来源于 财新 斯麓 | 文
1749年,也就是乾隆十四年,34岁的袁枚辞官养母,回到江南。这位24岁即中进士、得到乾隆帝青睐的一代才子,经过跌跌撞撞的十年坎坷的官场生活,仍然是一介县令。心高气傲,“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受挫,对官场疲倦失望的他在南京小仓山发现了一座废弃的“隋园”。这座大花园有山有湖,有村庄,有庙庵,有石洞,有竹林,有水闸,由于园主隋赫德后人的落魄,变得 “园倾且颓,驰其室为酒肆,舆台嚾呶,禽鸟厌之不肯妪伏;百卉芜谢,春风不能花”。 即使如此“蓬头垢面“,具有审美诗情的袁枚仍然慧眼看出园子的”不掩国色“,即买下作为归隐之处,决计退出倾轧虚伪的官场,回到自由洒脱的随性人生中,改园名隋园为随园,从此真正地做一回自己。

袁枚像
若干年后,和他的随园一同名扬天下的袁枚,在自己的畅销书《随园诗话》里提及了园子的另一位旧主人——历经四任江宁织造的曹家 (曾因为抄家,江南“住房十三处共四百八十三间,地八处十九万顷”全部被雍正帝赏给继任织造隋赫德) ,那曾经四次接驾康熙帝的百年豪门。虽然隔了近一百年,无从相见,他说金陵人至今仍记得曹家公子在秦淮河畔写诗的风华,且 “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 也许如他所说,这见证袁枚最精彩的人生下半场的由衰转兴的美丽随园,也就是曾经见证过《红楼梦》作者曹公的人生上半场的从兴转衰的大观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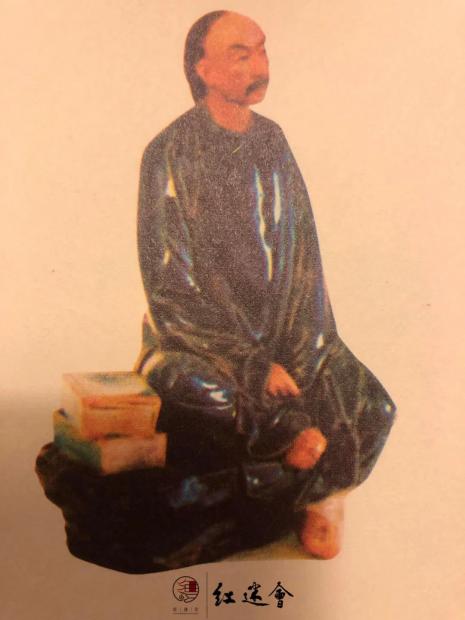
曹雪芹像
化身十几岁少年贾宝玉的曹家公子,和曾经宦海沉浮后的袁枚的志趣或许也相同,他们都想真正的做自己,过着随心而动的生活,这看似并不太高的要求却并不容易。
在他们的时代,主流入世的儒家知识分子的个体生活应该服从公共生活。他自身应该每日三省吾身的修身养性,他的家庭应该是克己复礼的三纲五常,而他的理想应该是明君贤臣,济世救民,创造一个清平盛世。一蔬一饭,儿女情长,那些人性当中的必然,明面上都可看作是不务正业。
当然,正统的冠冕堂皇之外,也不是没有非主流的个人自由的精神空间:红袖添香、吟风弄月,竹林桃源也是不少士大夫的另一个被挤压的自我,只是在正统的光伟正反衬下,左右无非是细枝末技,形状影影绰绰、语焉不详,或惊鸿一瞥进入诗词歌赋、戏剧杂曲、稗官野史,或冠以《警世通言》等名目荣登反面教材。或许这些情愫有可能像糖衣炮弹一样让人沉湎其中,破坏了家庭和公共事务当中可贵的自律和规则,进而还可能破坏心怀天下的使命感和责任心。

Photo by: timg
有趣的是,这些“糖衣炮弹”却被《红楼梦》以事无巨细的方式坦坦荡荡写成了明面,而那些限制个人的公共和家庭伦理,却鬼鬼祟祟地时隐时现。读者仿佛一个偷窥者,看到了本属于贾宝玉的纯粹个人的生活体验、家长里短和日常起居的记录;这还远远不够,贾宝玉仿佛拥有自己星球的小王子,大观园就是他的星球,一个洋溢着青春的生命的至美的个人乌托邦:如此奢华,富足,数不尽美好的雕栏画栋、美酒佳肴、戏剧诗歌,个性各异的才貌双全妙龄的女孩子中,有着他倾心爱着、也爱着他的人,还有更多爱护他包容他体贴他的家人、朋友和仆人;在物质、精神和情感上,这个不被正统社会所提倡的高度艺术和审美的完美世界,却是多少人暗自的梦想。
而乌托邦Utopia本身就是“eutopia”(美好的地方)和“outopia”(没有的地方)组成的,也就是如此美好的地方就不曾真正存在。

Photo by: KAI MA
年少的贾宝玉也许只是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不自知,如同只照”风月宝鉴“正面的贾瑞,他眼里只有五彩缤纷的美,即使能感受到那华林中隐约的悲凉,却不了解是什么支撑着这些美;但作者作为“翻过跟斗的人”,却时时刻刻提醒大家要照那面骇人的骷髅的反面,那才是真正的现实和生活的本质。把那些年少的他曾视而不见的滤掉的内容,尔虞我诈的家族斗争,步步惊心的政治环境,人情世故的社会规则,美人的不完美,青春的易流逝,命运盛衰的无常,悄悄写进字里行间,假做真时真亦假。直到有一天,美梦幻灭,风月不再,朱颜辞镜,子孙飘零,那承载乌托邦的大观园也变成废园。

Photo by: Shaoqi He
大部分人的一生,不曾经历兴盛,也无所谓衰败,而作者上半生众星捧月,见识过他那个时代最繁华的生活,而下半生只能在孤寂潦倒的痛苦度过。他终于明白,生命中无常和艰辛,对于每个人都一样,那些好与坏、生与死、兴与衰,从来不是一成不变。连曾经引以自豪的不通世俗经济,都成了追悔莫及的忏悔。个体是永远无法脱离时代环境而遗世独立的,任何乌托邦都不能脱离残酷的现实。
此时此刻,他才找到了生活的真相,理解了那比起风花雪月的体验更为深刻的真相,尽管让他付出沉痛的代价,也让他在这痛苦中开出了之前家族百年的繁华生活都不曾开出的动人的花朵——用血泪酿成的妙笔,把家族经历过的光彩和黯淡写成了文学史上伟大的绝唱。

Photo by:Shaoqi He
曹家的故事结束了,园子的故事却没有。官场不得志的文人袁枚的后半生似乎是贾宝玉的前半生的延续。与贾宝玉不同,袁枚早年是想追求主流价值的成功,当过科举英雄,也曾努力做个好官,实现清明盛世的抱负,却终究发现自己洒脱的性情终究不适应当时的政坛,于是不再恋栈,及时收手依从自己的心灵,用后半生着手建造自我的精神乌托邦。
接手凋零的随园后,袁枚不是哀伤他的枯草衰杨,而是一点一滴用心建设和经营,把自己的怡然的生活情趣和随性的文学意趣寄托于此, “茨墙剪园,易檐改途。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夹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就势取景” ,先后恢复和新建了香雪海、群玉山头、绿晓阁等20余处迷人景致,随园成为当时金陵文人骚客的雅集欢宴之地。同时,他拆掉随园的四面围墙,每逢佳日,火树银花,游人如织,袁枚不加管制,与众乐乐,广交朋友,更在门联上写道: “放鹤去寻山鸟客,任人来看四时花。”

Photo by: Demi He
十年仕途的沉浮历练,也经历过家贫掣肘,他已经不是什么不问俗务经济的仙人,世事洞明皆学问。 几次大的整修用尽了他的积蓄,随园用来的维护和改造的巨额资金全靠他商业头脑和“直播带货”:曹公对大观园的承包经营的设想变成他的日常:袁枚将“园东西之田地、山池分十三户承领种植”,任其种稻蔬果木、养鱼放鸭,不仅每年可收取租金,平日生活所需的食物,基本都能由佃户供应自给;园子初具声名、有了不少游客后,对饮食颇有研究的他就写了一本《随园食单》,渲染了私园的就地取材的和家厨烹调的精妙,将筵席设在亭台轩榭中,外有美女伴唱伴舞,游人纷至沓来,随园立即成为“网红打卡店”;同时,他还在园子里印刷出版出售自己的著作,题字卖画、开学堂,收入颇丰。
大观园那种诗话,曲艺,饮食,建筑,园林,文人墨客融为一体的风雅在随园重现。连乾隆第二次南巡的时候,两江总督都要求把它作为行宫。面对这样邀宠的宝贵机会,已经对政事心冷、不问东西的袁枚清高地婉拒了,让随园避免了大观园一样接驾的命运。平头百姓随意出入,九五之尊却被拒在门外,或许在他心中,随园始终是他一个人的精神自留地。
在随己任性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当中,他诗情文采的天才被激发出来,放浪形骸,颠倒众生,成就了随园的袁枚,也成就了他自己。他不仅是诗坛盟主,文学大家,也是在园林、茶艺和美食都颇有建树的清代第一流才子,随园是他永恒的缪斯。在保护了那份脆弱易散的美丽的同时,袁枚终于实现了在主流世界当中未曾实现的自我。

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康乾盛世的回光返照下,他精心营造那一个人的精神乌托邦虽然映衬着落日余晖,却依然无法挽回时代的巨轮。终生守着随园,走完82岁高龄并葬于此的袁枚,有幸没有看到19世纪后半段的动荡不安。山河破碎,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也留不住一个避乱的桃花源。少了知己的随园又走向了衰败,太平军把它夷为平地用来种地,来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一个人的乌托邦,终究伴随着关起门来的太平盛世乌托邦一起毁灭。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个人的乌托邦从来不曾真正独立存在,或许需要一个更宏大坚实的公共领域的乌托邦的照拂,但所有的乌托邦尽管梦幻般绚烂,也都免不了走过希望、失望和重振旗鼓的艰难历程,都不能许愿没有痛苦的人生。而完全没有了乌托邦的世界,没有臻于致治的美好愿望和进取,也不会有失败和幻灭后的深刻领悟和理解,而那些则组成了人生最美丽最极致的部分。袁枚和曹公就因此用各自的方式终究成全了自己,尽管也许都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乌托邦不是一个人道路的终点,它就是道路本身。
话题:
0
推荐
财新博客版权声明:财新博客所发布文章及图片之版权属博主本人及/或相关权利人所有,未经博主及/或相关权利人单独授权,任何网站、平面媒体不得予以转载。财新网对相关媒体的网站信息内容转载授权并不包括财新博客的文章及图片。博客文章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财新网的立场和观点。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